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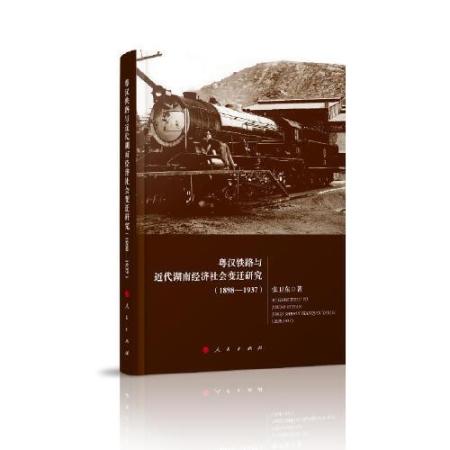
近年來,“交叉研究”成為學(xué)術(shù)界呼聲很高的熱詞,無論自然科學(xué)界還是人文社會科學(xué)界,都在大力提倡跨學(xué)科、跨專業(yè)的“交叉研究”,并將這種“交叉研究”視為提升學(xué)術(shù)創(chuàng)新效率的一種重要方法。實際上,“交叉研究”并非一定是在不同學(xué)科、不同專業(yè)之間的交叉融合,在同一學(xué)科、同一專業(yè)內(nèi)的不同學(xué)術(shù)研究領(lǐng)域、研究方向之間,同樣存在著“交叉研究”的可能。通過對同一學(xué)科或同一專業(yè)內(nèi)不同研究方向、不同研究領(lǐng)域之間的溝通整合、交叉共融,同樣可以實現(xiàn)學(xué)術(shù)研究創(chuàng)新的目標(biāo)。湖北省社會科學(xué)院張衛(wèi)東研究員《粵漢鐵路與近代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研究(1898—1937)》(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,以下簡稱“張著”)一書就是這樣一部充滿“交叉研究”特色的學(xué)術(shù)新作。通讀張著,對于其中諸多創(chuàng)新性的學(xué)術(shù)觀點,筆者固然感到欣喜不已,但更令筆者感興趣的是,該書所體現(xiàn)出來的“交叉研究”的學(xué)術(shù)思路和傾向,因為這也是筆者近年來所極力向往的史學(xué)研究方法,盡管我們還不能武斷地認(rèn)為“不交叉,無創(chuàng)新”,但“交叉研究”有助于大幅提升創(chuàng)新性研究的效率,已經(jīng)屢屢得到證明,張著如今又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。是以筆者不揣谫陋,僅就張著所呈現(xiàn)出來的“交叉研究”特色,略談一點感想。
其一,該著體現(xiàn)了學(xué)術(shù)熱點領(lǐng)域之間的“交叉研究”。盡管鐵路進(jìn)入中國的時間比較晚,但在自從交通史研究學(xué)科于近代誕生以來,鐵路史研究便一直成為這一學(xué)術(shù)領(lǐng)域的熱點問題,這一方面既是因為隨著交通史研究的深化,其研究領(lǐng)域也不斷有所拓展的緣故,另一方面也因鐵路對近代中國而言,可謂牽動社會方方面面的事物。無論是研究中國的近代化問題,還是專業(yè)性更強的交通史問題研究,鐵路都是無法繞開的話題。因此,鐵路史研究之成為交通史研究學(xué)科的學(xué)術(shù)熱點領(lǐng)域和新的學(xué)術(shù)增長點,便順理成章。如今在中國的高鐵建設(shè)已然成為國家一張靚麗名片的時代背景下,鐵路史研究的熱潮勢必將進(jìn)一步高漲和持續(xù)。以言“近代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”,其選題屬區(qū)域史范疇自是不爭,而區(qū)域史的研究自上個世紀(jì)八、九十年代起,始終是歷史學(xué)研究的熱點領(lǐng)域之一,至今而未曾稍歇。張著的兩個核心語匯,一為“粵漢鐵路”,一為“近代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”,皆在學(xué)術(shù)熱點領(lǐng)域范圍之內(nèi)。因此,稱之為學(xué)術(shù)熱點領(lǐng)域之間的“交叉研究”,可謂允矣。
其二,該著體現(xiàn)了政治史、經(jīng)濟(jì)史、社會史、文化史多方向的學(xué)術(shù)“交叉研究”。仍以張著的兩個核心語匯而論,無論“粵漢鐵路”,還是“近代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”,都不是單純的經(jīng)濟(jì)史領(lǐng)域的問題,而同時也是特定政治、社會、文化領(lǐng)域的問題。以粵漢鐵路而言,其在打通廣東沿海與湖南、湖北等內(nèi)陸省份之間經(jīng)濟(jì)交流溝通的脈絡(luò)上,確實具有經(jīng)濟(jì)方面的重大價值,但是鐵路的貫通,所打通的又豈止于經(jīng)濟(jì)呢?政治上、軍事上、文化上的溝通與往還,也因此而更加順暢,乃是毋庸多置唇喙的事實,如果我們說隨著粵漢鐵路的通車,鐵路沿線各省之間、南北中國之間的社會、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軍事、文化更為緊密地聯(lián)系在一起,又有何不可呢?以“近代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”而論,近代湖南在鐵路貫通之后,所發(fā)生的變化亦不止于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兩項,而是一種全方位的變遷,大到軍事、政治、文化,小到普通居民的衣食住行,又有哪一方面不受到影響呢?以此言之,將張著稱為一部融合政治史、經(jīng)濟(jì)史、社會史、文化史等多方向的學(xué)術(shù)“交叉研究”論著,可謂當(dāng)矣。
其三,該著體現(xiàn)了具體實證研究與抽象理論研究之間的“交叉研究”。歷史學(xué)研究最強調(diào)言必有據(jù),所謂“言必有征”,即是說實證性的研究為一部成功的歷史學(xué)論著所不可或缺的要素,張著所體現(xiàn)出來的“實證性研究”要素,可謂通篇滿幅,在在皆是,以其所論核心概念“鐵路(粵漢鐵路)”“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”,都是建立在大量具體史料的實證基礎(chǔ)上而形成其觀點的。另一方面,歷史學(xué)研究又不能止于簡單的“實證研究”層面,還必須對“實證研究”的結(jié)論進(jìn)行理論的抽象概括,以從中發(fā)現(xiàn)歷史演進(jìn)的內(nèi)在邏輯,如眾所周知的“鐵路文化”“湖湘文化”,就是建立在鐵路史的實證性研究以及對湖南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文化等多個領(lǐng)域進(jìn)行實證性研究的基礎(chǔ)上,提煉升華出來的一種理論性的總結(jié)。綜觀張著,既有對于“粵漢鐵路”“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”等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,也有在此基礎(chǔ)上對“鐵路文化”“湖湘文化”進(jìn)行抽象化理論總結(jié)的嘗試,是以稱之為具體實證研究與抽象理論研究的“交叉研究”的史學(xué)論著,可謂不虛。
其四,該著體現(xiàn)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(jié)合的“交叉研究”。所謂宏觀研究,是指其將研究論題置于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大背景下進(jìn)行思考,無論是“粵漢鐵路”這個物質(zhì)性的具體物象,還是“近代湖南經(jīng)濟(jì)社會變遷”這個抽象性的文化現(xiàn)象,張著都是將其放到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宏大時代背景下進(jìn)行觀察和剖析的。所謂微觀研究,則指其通過對具體的事件、人物進(jìn)行細(xì)致的剖析,通過兩者的交叉融合,從而將整個研究落于實處。僅舉湘米銷粵為例,便可清晰地看到其宏觀思考與微觀考察相結(jié)合的學(xué)術(shù)思路和研究途徑,一方面湘米銷粵在宏觀層面上反映出湘、粵兩省的經(jīng)濟(jì)形態(tài)差異之一斑,另一方面又從微觀上考察了湘米運粵的細(xì)節(jié)性問題,如“湖南全省稻作面積產(chǎn)量及畝產(chǎn)比較”“1914—1938年湖南稻米產(chǎn)量”“1904—1933年湖南海關(guān)谷米出口情況”等諸多統(tǒng)計表格中的數(shù)據(jù),更是細(xì)致而微,從中讓我們了解這個時段中湖南的稻作面積、畝產(chǎn)量、稻米總產(chǎn)量、谷米出口數(shù)量等具體情況,從而獲得湖南省在這個時期中糧食生產(chǎn)乃至經(jīng)濟(jì)運行的情況。由此言之,稱張著為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(jié)合的“交叉研究”,可謂實錄。
張著如此傾情于“交叉研究”,其意義又何在呢?這既體現(xiàn)出作者敏銳的學(xué)術(shù)嗅覺,也是作者學(xué)術(shù)功力的體現(xiàn),據(jù)作者在《后記》中的相關(guān)敘述可知,作者曾經(jīng)進(jìn)行過一段時間的古代史的研究,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研究成績,后來又因緣際會轉(zhuǎn)入中國近代史領(lǐng)域,這個學(xué)術(shù)轉(zhuǎn)向本身就預(yù)示著作者在學(xué)術(shù)研究的道路上出現(xiàn)“交叉研究”的潛在可能,古代史研究對史料搜羅和剖析的微觀性更強一些,近代史的研究則多了幾分宏觀的思維,兩者交叉融合,最終便體現(xiàn)在這部長達(dá)42萬余言的巨著中,可謂得其所哉!
(作者系揚州大學(xué)社會發(fā)展學(xué)院教授、博士生導(dǎo)師)
來源:中國社會科學(xué)網(wǎng)